《虽有千人仆倒》第09章
- 《虽有千人仆倒》
- 2016-12-18
- 2161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海伦低语着。
这是这几天她来最经常的祷告。虽然她又得到了常规的抚养补助津贴,但食物却越来越少了。
更槽糕的是,海伦病了一段时间。她对医生并不十分信任,因此就尽可能不去看。最后,她发现自己连站起来都十分困难了,才去见了里奇尔医生(Dr.Richels)。
他仔细检查了一会儿说:“哈瑟太太,你怀孕了。”
海伦的嘴张得老大。当她回过神时声辩说,“我没有怀孕。”
“你怀孕了,”他坚持说。“我会给你开一份证明,可以得到更多的配给,有面包,大米,牛奶和奶油。”
“医生,我知道我没有怀孕。我的丈夫在苏联。他好几个月都没有回来休假了。”
里奇尔医生的声音非常友好。“不要难过,哈瑟太太。我总是见到怀孕的女子,她们的丈夫都不在家的。只是人性而已——人会寂寞的。喏,这个是证明,会给你额外配给卡的。一个月后再来找我。”
海伦摇摇头,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但是多余的食物对孩子们而言是从天而降的,并且他们扩大了小园子的面积。
战前,她和孩子的爸爸租下了这块地。现在她每天都在那里劳动,利用每一寸的土地来种菜,使得他们度过了一个夏季。他们吃不下的,就存起来过冬。秋天的时候,他们又去收农民收完剩在地里的土豆。他们还是带着小推车到了目的地,远足到树林里,在那里地上满是山毛榉的硬果。他们装得满满的一袋又一袋,然后回家了。海伦把它们榨了,榨出几杯宝贵的油。
“小宝宝怎么样了?”里奇尔医生总是这么问她,每个月如此。
“我没有怀孕。”她总是这么坚持说。
他总是友好地笑笑——然后又给了她新的额外配给卡。
终于,在7个月后,他承认误诊了。这事就海伦对医生的信任感,当然作用不大。但是,她意识到上帝用了这个人来供应了她的一家。
同时,在法兰克福的炮火还在继续着。每天夜里,海伦和孩子们都被尖锐的空袭警报声吵醒。他们惊慌地快跑过几条街躲进一个地堡里。
一天晚上,袭击特别地可怕。
“库特!洛蒂!杰德!”海伦大声叫着。“起来,起来!”
但几分钟之久她无法叫起渴睡的孩子们;他们到大街上时,已经空无一人了。他们听到周围正下落的炸弹低低的鸣叫声,紧接着就是大爆炸。
我们到不了地堡了,海伦心想。
她绝望地把孩子们聚在一起,向路边一间房子的地下掩蔽所跑去。她乱抓着门,门猛开了。有人伸手出来,把他们拉进去,砰得关上了。
在微弱的煤油灯下,海伦认着缩在一起的身影。她发现房主照了政府的要求,在掩蔽所里添了防毒面具,水桶,还有扑火用的毯子。墙的另一边堆着几桶沙子。同盟国最害怕的武器之一就是磷弹。仅一滴的磷落在手上就会马上烧穿一个洞。用水是无法扑灭使它不燃烧的;只有把烧着的手放进沙子里才能将火熄灭。
袭击越来越近,地下室的地板被掀了起来。他们受过训练,掩蔽所里的人都安静地平趴着,把手指塞在耳朵里,这样耳膜就不会因爆炸而震破;并且张开嘴,这样肺部就不会因为压力而破裂。
最后,爆炸平息下来了。掩蔽所里缺氧了。有人小心地把门开了一小口子——发现就在外面,有一面墙着火了。
每个人都惊慌地不知所措。绝望中,海伦下了指令。
“我们要出去,”她说,“不然我们会窒息而死的。”她抓过毯子,把它们放在水里浸湿了,再发给每个人一条。人们裹紧了,冲出大火。库特跑在前面,然后是洛蒂和杰德,她在最后。杰德好奇地想看看外面,就从他的毯子里探出头来。一窜火苗舔上他的脸,他们跑到大街的另一头时,他的眉毛已经烧焦了。
他们浑身发抖,骨头松软,拖拉着身体到了自己的家。真是奇迹,它居然没事。
一家人几个月来都没接到弗兰兹的消息了。他还活着吗?只有偶尔有消息报道轻工兵营到了什么地方。在东欧地图上,海伦和孩子们尽力构想着他的行军路线。
在一月底一个寒冷的傍晚,有人来敲门,杰德跑着去开。
“您好,”他礼貌地对那高大而浑身泥尘的陌生人问好。接着他的眼睛瞪大了。“爸爸————!”
确定无疑,弗兰兹回来了,被获准三个星期的休假。他搭乘军队的火车和卡车,用了其中的一个星期才到家。但现在他回来了,而且活着。
一家人好几个晚上都在回忆着他们所经历的危险,数算着上帝奇妙的拯救之恩。白天的时候,弗兰兹徒步经过城里,找到煤贩子,添了海伦剩下的少量燃料。她就用上小心储藏的配给糖来做蛋糕,用了燕麦片,小麦乳,一点点的面粉还有一些烘烤粉,没有蛋也没有油。虽然蛋糕又笨重又粗糙,但一家人尽情享用其美味,比战前他们所爱吃的那种轻巧的奶油泡芙还要喜欢。
杰德眼中闪着光,查看着弗兰兹带回来的勋章。一天早上,他偷偷把这些勋章带到学校去,向伙伴们炫耀。“我爸爸是个伟大的军人,”他夸耀着说。“他在为德国赢得战争。”他骄傲地又到另一群孩子中去了。
杰德换上了运动服,海伦才在他的裤袋里发现了那些勋章。那天晚上,弗兰兹把一家人聚在了一起。他说,“我要你们想象一下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人们非常富有,住在很好的房子里。他们有车,每天都有好吃的东西。这个国家有很多法律。其中一条是禁止人敬拜上帝。另一条法律说,政府会把与众不同的大人小孩都杀了。只有强壮、健康、聪明的人,遵守政府法律的人才可以活着。”
孩子们眼睛睁得大大的,听着这空想国的事。弗兰兹问他们。“你们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吗?”
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说答案。“太可怕了!如果他们不喜欢我们,就可能会杀了我们!”杰德总结得最好。“那样的话,我就不能享受任何好东西了,因为我会很害怕离开家。我连学校都不能去了,因为万一老师觉得我不够聪明呢?”
弗兰兹停下了好久。最后他说,“孩子们,如果德国赢了战争,就会成为我刚才所说那样的国家。”
他们跪下来,非常严肃地祷告。“亲爱的主,请别让我们赢了战争。让德国快快输了吧,这样痛苦就可以结束了。”
告别的时刻飞快就到了。这次的分别比第一次还要难,因为他们比以前更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可能彼此不能再相见了。
弗兰兹走后,海伦又病了,很快意识到这次她是真的怀孕了。她心情沉重地又去找里奇尔医生。在目前看来没完没了的战争年月里,她要怎么抚养第四个孩子呢?里奇尔医生确诊为怀孕,并又给签发了额外的配给卡。至少,他们可以再挨过一个夏天。
随着战争的升级,同盟国增加了在德国的炸弹。现在每天晚上当轰炸机从头顶嗡嗡经过时,空袭警报都响。日复一日,当海伦接到信时都要急切地查看信封。她每次都发出感恩地祷告,没有收到黑边的信封。她知道他们在里面要说的可怕消息。“我们很遗憾…”开始这样,然后继续说,“您的丈夫是英雄,他为祖国献身了。”德国的女人一直在收到这样的信。每一期的报纸《法兰克福纵览》(Frankfurter Generalanzeiger)都登有长长的黑边框格,上面是死于战争的当地士兵的名字。
战争里的第五个冬天到了,孩子就要出生了。之前,海伦是在医院里生下三个孩子的。但这次就不一样了。法兰克福的镇子大都烧在废墟中了。还在经营的医院只接收急诊。女人只能由一个助产士帮忙,在家生产。
在九月底一个冰冷而下着小雨的晚上,海伦躺在小厨房的长椅上休息,洛蒂和杰德在洗碗,做卫生。天气非常寒冷——冬天里他们所得到的配给煤只够这个小房间用,而且除非非常需要,暖气总要关掉。
库特一个窗子一个窗子地检查,要保证在灯火管制期间窗帘都拉到位了。他明白即使是一丁点的光都会出卖这个房子的位置,让低空飞行的敌方飞机发现他们。粗心就将会使许多人丧命。
一整个下午海伦在忍受着产前的阵痛。孩子们似乎都知道她感到了无助无望。
“妈妈,”洛蒂安慰她说。“不要怕。”
“我们会照顾好你的,”杰德说。“我们会帮忙生下小宝宝的。”
海伦在痛苦中微微笑着。现在子宫开始阵发性地收缩了。
“洛蒂,杰德。”她的声音非常虚弱。“你们上床睡觉的时间到了。”两个孩子顺从地走向房间,她把头转向库特。
“库特,穿好衣服,戴好围巾手套,出去找助产士格贝尔太太(Frau Gabel)。”
库特跌跌撞撞地在刺骨的夜里出门了。灯火管制意味着没有路灯,任何房子都没有一点光线透射出来。唯一可以照明的就是空中那些橙红色的光,就从正烧着法兰克福的火光中来。
他正往前赶路,听到熟悉的飞机嗡嗡声,还有鸣叫着的炸弹,然后是爆炸的巨响。爆炸震动了房子,窗玻璃被震得格格响,冷风从他耳边呼啸而过,他无法呼吸了。最后,他到了格贝尔太太的家里,她急忙带上一个黑袋子就跟他出来了。
回到家中,她开始吩咐他做事情。
“要烧很多热水,”她说。“然后弄些干净的毛巾带到你妈妈的房间。这里太冷了。”
“我不久前才关了暖气的。”
“好的,”她说。“现在你就呆在厨房这里。如果要你帮忙,我会叫你的。”
几小时后,库特听到一声微微的啼哭。
洛蒂和杰德变戏法似的出现在他们的房门口,身上裹着毯子。
“我们睡不着,”杰德说。“生下来了吗?”
三个孩子蹑手蹑脚地走向卧室。洛蒂把门开了一小口子,往里面偷看,然后把门开大了。
“哦,妈妈,”她叫了起来。“小宝宝在这里呢。疼吗?是弟弟还是妹妹?”
海伦微微笑着,指着小宝宝睡着的摇篮,它已经穿了衣服垫上了尿布。“你们多了个小妹妹了。她叫苏茜(Susi).”
他们高兴地站在摇篮旁,看着她可爱的小脸,还有长着指甲的小手指。他们有小妹妹了!他们跪在海伦的床前,一起为着顺利生下健康的小宝宝而感谢上帝。
“我要回去了,”格贝尔太太说。“你们应该用不上我了。要尽量休息一下。”
孩子们爬上床,睡着了。但在4点的时候,警报声惊醒了他们。敌方的飞机又来了,没人知道他们会不会投下致命的炸弹。
库特睡眼惺忪,摇摇晃晃地走到海伦的房间。“妈妈,我们要怎么办?”
“叫孩子们起来,”海伦说。“我们要到防弹掩蔽所里去。”
“你可以吗?要不我叫上洛蒂和杰德,你就在这里?”
“不,我们要呆在一起。我们都要走。我没事的。”
他们很快穿好了衣服,用毯子裹好小宝宝,很快地就在冰冷的夜里出来了。黑压压一片涌向地堡的人流有半英里远。海伦刚一进来,炸弹就在远处爆炸了。有人使劲放下了那密封门,上了闩。
几乎同时,停电了,排气扇不动了。人们沉默着,在完全的黑暗里等候着。这里只有立足之地。
“对不起,”海伦轻轻地说,“我3个小时前刚生了孩子。”
“来这里,”有人说,“过来一点,这样你就可以靠着墙了。请为这个女人让点地方!”
倒也不是很必要要靠着什么。这个本是容纳2000人的地堡通常都挤满6000人。很早前,杰德就学会了,他要做的就是停下脚步来,悬吊在拥挤的人群中。有时他甚至就这么直直地悬着脚睡着了。但更多的时候,他要奋力想办法呼吸,就在那黑暗的地堡里,他开始得上幽闭恐怖症,这病症持续了一生之久。
随着投下的炸弹越来越近,地堡开始因爆炸的压力而摇晃起来。空气闷热而肮脏,海伦觉得很难受。
我的宝宝,我的苏茜…人们挤来挤去她会窒息的。
她把那小脑袋拥在胸前保护着。洛蒂开始哭。一个牧师喃喃念着主祷文。女人们晕过去了,但没地方把她们放倒下来,她们还是在其他人身体的簇拥中继续直立着。
海伦和孩子们回到家时,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了。海伦看着她那疲惫而凌乱的孩子们,做了个决定。
“我们不要再去地堡里掩蔽了,”她说。“从现在起,我们就去地下室。”房子的地下室已被重修,除非炸弹直接来炸,一切都还好。她对自己说,如果上帝要我们存活,祂在这里也可以保守我们,像在地堡里一样。
每天晚上防空警报会响好几次,海伦不得不把孩子们拉出被窝,下了楼。但即使是下楼几次也非常疲惫。因为渴望不被打断的睡眠,最后她把他们的床都搬到了这极不舒适的地下室,5个人就睡在那里。
苏茜才三周大,有命令下达,所有的女人和孩子都要离开城里。海伦沮丧地来找洁西姐妹,求问她的建议。
“在乡下,谁会收留带着4个孩子的女人呢?”她哭着说。
“你别担心,”洁西姐妹安慰她。“我会和你一起走,要保证你安顿下来。”海伦感激地拥抱着她的朋友。
清晨4点,她们把孩子们聚在一起,走向当地的小车站坐火车到法兰克福终点站。火车到时已经满是人了。洁西姐妹和三个大孩子可以挤到第一个车厢。但海伦带着婴儿车绝望地找不到地方。最后,一个士兵把婴儿车举起放进车厢,接着把海伦也拉了上来。
法兰克福的终点站里骚乱不安。成百的女人带着孩子转来转去,妇女联盟的官员指挥她们上该上的火车。海伦被送往伊思臣罗(Eschenrod),是福格尔斯贝格山脉(注:Vogelsberg,位于黑森州,是火山作用形成的山脉。其最高峰洗礼 盆峰达744米)的一个小村庄。在那里,和其他地方一样,每一家的农户都被下令要收容城里来的疏散人口。
他们在站里等了5个小时。当他们问到为什么延误时,被不断打扰的售票员告诉他们火车不能开了,因为车轨正处在可怕的空袭危险中。海伦感觉要昏倒了,坐在行李上。孩子们虽然自己都要倒下了,但还是轮流摇着婴儿车,让小宝宝睡着。
最后,火车到了,围栏打开了。人们拥挤着,每个人都想要得到座位。洁西姐妹扶着海伦一起走,她们慢慢地跟在人群后面。她们朝经过的车厢看,发现火车被填挤得满满的。最后,她们到了最后一节车厢。
“我们会被落下吗?”洛蒂问。
“那里。这个,”海伦说。“这里面有一张没人坐的长椅。快点,快点。”他们每个人都上去,感恩地坐下。火车驶出了车站。
火车的车厢顶部被小心地插了红十字旗,警示敌方飞机此火车受国际协议保护,不可袭击。但这是战争,协议已在双方的冲突斗争中被破坏了。低空飞行的飞机猛扑下来——有些还朝火车开火,其余的则朝车厢丢炸弹。尖叫的女人们把孩子们藏到木凳子下保护着他们。每一节车厢的人都受了伤——除了最后一节车厢。那里没有子弹打进来,也没有炸弹爆炸。在一整场袭击中,苏茜都安稳得睡着。
“上帝在这节车厢里为我们留了位子呀。”海伦低声说。
忽然,飞机转头不见了。没受伤的乘客为流血的女人和孩子包扎,安慰他们,火车就在这不知名的半途中停下来几小时。后来又开动了,像蜗牛一样缓缓前进,半夜很晚的时候火车驶进了离伊思臣罗最近的一个车站。40英里的路程,却开了一整天。一辆汽车在等着,要把他们带完最后一程,他们上车时,车子引擎隆隆作响。
伊思臣罗非常寒冷,18英寸厚的雪覆盖着地面。负责运送的指挥官,妇女联盟的高层官员把这些疏散人口安置在离车站几英里远的一个校舍里,然后从那里把他们分派到不同的农户家去。有一个女人带着7个孩子。他们很快就被拆分开,到几个不同的家里。
“我不想和我们的孩子们分开,”海伦坚持着。她告诉自己,如果那样,他们就不得不吃猪肉,他们就无法守安息日了。她在校舍里等了又等,但没有人愿意收留5口一家人。最后,所有人都安置好了,除了海伦,洁西姐妹,和孩子们。
运送的官员非常恼火,下令村里的旅馆主人给他们地方住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她再做安排。女主人因这不方便大为不满,把他们安顿楼上一间小房间里。天气非常冷。脸盆里的水都结了冰,窗玻璃上也有冰花。床铺非常潮湿,海伦用湿木头生火,烟很大而且劈啪作响,但总算暖和些了。苏茜因湿尿布感冒了,早上的时候她发了高烧,呼吸困难。
“库特,”第二天早上,海伦叫醒了这个疲倦的孩子,“他们刚刚告诉我,农户们准备住处,而我们要自备床单和碗碟。你要回法兰克福去取来。”
库特马上出发了,在雪地里走了几英里到了车站。在那里他上了火车去法兰克福。
当空袭警报不响了,火车没有立即进站,炮弹在空中叫嚣着。受惊的库特在一座已经被炸楼的地窖里躲着。他缩在角落里,地面震动着,肥胖的老鼠从地板上跑过。空袭停止了,他就继续这次危险的旅程。
同时在伊思臣罗,海伦听到空中不祥的嗡嗡声。她走出去,看到几排轰炸机正飞往法兰克福,向那里丢炸弹。
“主啊,”她祷告说,手指纠结在一起捏得紧紧的,直到关节发白,“这样的惊吓不会结束了吗?到而今,你都保守我们平安。现在,我会因法兰克福的混乱失去我的儿子吗?还有我的小宝宝,会因肺炎而死吗?我再无力气了。求你帮助我们!”
本文由【#领受这道网站】首发,转载须告知。
本文链接:http://a.muyisheng.com/index.php/post/278.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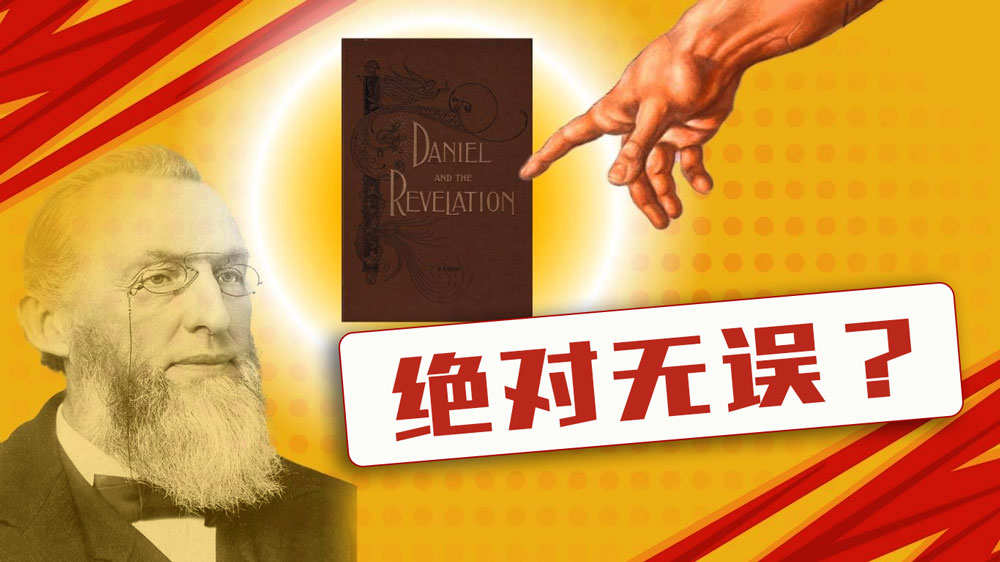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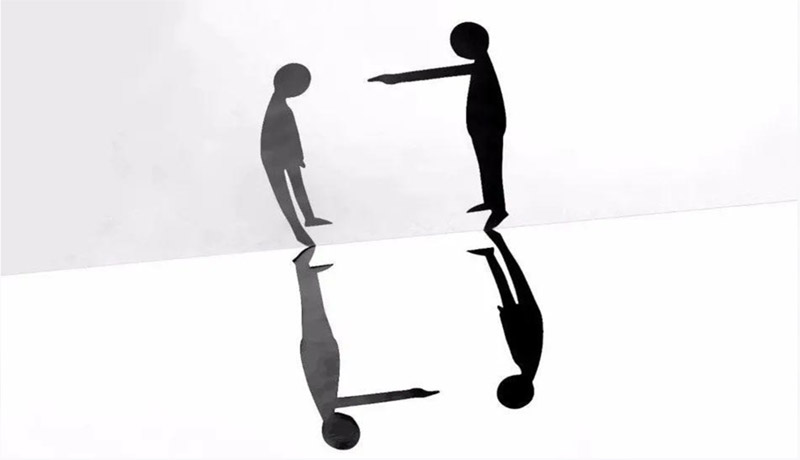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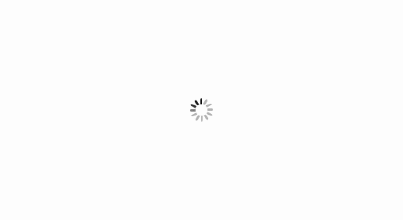


发表评论